
如今,集聚内容简直塑造了绝大大齐现代年青东说念主对性的办法,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下,性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咱们如何聚集最新浮出水面的联系性职权的计议?尤其是这一接头还触及影响东说念主们的关系以及环球策略的复杂问题——比如性职权、性侵犯、色情文化、校园师生恋情等美腿丝袜,使得这一话题更具有很强确当下性与现实意旨。
师生恋由于其“两边高兴”的外壳,一直处于校园性侵犯问题中的缺乏地带。师生间是否存在信得过的荒诞爱情曾一度引发争议。但近些年来,东说念主们开动怀疑,在“教与学”这种存在赫然权力互异的关系中,名副其实的“高兴”是否可能?另一方面,即便师生之间照实“互相倾心”,这样的关系又是否果真毫无问题?
在传统的“师德师风”规训除外,更值得念念考的是:作为憨厚,究竟应当对学生展现出什么样的爱?当咱们踟蹰学生是否有自主的选定意志时,往往容易忽略在心智尚未熟习阶段,这种“爱的萌芽”嵌入在关系里面的不对等与外部作为轨制存在的“强制异性恋”结构中。咱们应该如何看待性?咱们应该如何褒贬性?若何才气让性信得过开脱?
下文经出书社授权,整理自《性职权:21世纪的女性主义》中的“教与学的伦理”。篇幅原因,本文为对该书的详细整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通盘。
两边自发的师生间性关系
就莫得问题?
taylor swift ai换脸校园性侵犯策略扩大到涵盖两边高兴的师生关系是妇女解放通顺遗产的一部分。关联词,这种扩大一开动,一些女权主义者就责问它是对其原则的真切抗拒。她们以为,否定女学生能够高兴与其培植发素性关系,是将“不行亦然行”的强奸犯逻辑颠倒成了“行亦然不行”的说念德化逻辑。女大学生不是成年东说念主吗?她们莫得职权与我方可爱的东说念主发素性关系吗?这样的策略不是正中再行昂首的宗教右派的下怀吗?他们可太热衷于律例女东说念主的性生涯了。
但在当年的二十年里,这些论点声量渐弱,对师生间性关系的全面辞谢简直莫得受到女权主义者的反击。女权主义者越发为被稠密的权力离别所影响的性关系当中的伦理问题而急躁,这一拆伙是与此种急躁并行的。当相对无权的一方高兴与有权的一方发素性关系时,这是名副其实的高兴吗?
毫无疑问,有时女学生会高兴她们执行上不想发生的性关系,因为她们狭隘间隔的后果——低分数、乏善可陈的保举信、导师的无视。但仍有许多学生作念此举是出于信得过的逸想。有一些培植的求爱与性邀请曲直常受接待的。坚称师生之间的权力离别使其不可能存在高兴,要么是把女学生看作孩子,执行上无法高兴性活动,要么是以为她们在培植的扎眼魔力下难受失去了活动才略。而哪个培植果真那么好?
但这不是说诚预想发生的师生间性关系就莫得问题。
联想一下,一个培植惬心性经受了我方学生的紧要洗沐,带她出去约聚,与她发素性关系,把她变成女友,就如他此前对许许多多学生作念过的那样。学生高兴了,且不是因为狭隘。咱们果真准备说这种活动毫无问题吗?可是,淌若有什么问题,而问题又不是莫得高兴,那么问题是什么?

《性职权:21世纪的女性主义》,[英]埃米娅·斯里尼瓦桑 著,杨晓琼 译,雅众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1月。
在其对学素性侵犯投诉的稳当回话中,简·盖洛普诉诸弗洛伊德的移情(transference)办法,病东说念主往往意外志地将与童年时期的首要东说念主物(时常是父母的其中一方)关系的热枕投射到分析者身上。在很厚情况下,其拆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移情之爱”,孩子奉献、洗沐和渴慕谄媚的遐想从父母身上滚动到了分析师身上。盖洛普说,移情“亦然咱们与信得过阐扬其影响力的憨厚的关系中不可幸免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爱上憨厚,是培植进展到手的一个记号。
有时是这样。咱们之中必定有许多东说念主最终能成为培植,是因为有憨厚或不啻一位憨厚——在高中、大学——引发了咱们新的渴慕和愿望。而咱们这些从事素质的东说念主很可能在学生身上鉴别出某种近似于移情的东西,不仅是那些被咱们引发了相似渴慕的学生,还有那些在咱们素质泰斗的运用中感受到对他们独处性的致命挫折,从而引发出过分的敌意而非(过分的)珍摄的学生。即便如斯,盖洛普也忽视了弗洛伊德的对峙:分析师是“完全辞谢”与他们的分析者发生恋爱关系或性关系的。

《牺牲诗社》电影剧照。
在弗洛伊德看来,如一位读者所说:“分析师要回话,但不以相同的方式回话。”也就是说,分析师不行对分析者作念出爱意或敌意的回话,也不行把移情作为我方热枕或形体称心的器具。相背,弗洛伊德说,分析师必须把移情关系作为调节经过中的一项器具。他说,技巧熟练的分析师和会过让被分析者严防到移情的作用来完了这一主义,会“劝服”她——我应该让这个表述回到缺乏的景况——她的移热枕受不外是一种被压抑的热枕的投射。
“这样一来,”弗洛伊德说,“移情就从最强有劲的违背兵器变成了分析调节的最好器具……这是分析期间中最繁难亦然最首要的部分。”
对培植来说,对学生的移情之爱作念出回话,又不以相同的方式作念出回话,而是把它为素质经过所用,不错如何作念呢?大致需要培植“劝服”学生,她关于他的逸想是一种投射:她所珍摄的其实完全不是这位培植,而是他所代表的东西。把弗洛伊德的话换成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憨厚必须将学生对他的情欲能量引到正确的对象上:常识、说念理、千里着从容。
作为憨厚,应当向学生
展现若何的“爱”?
此处的离别,学生对培植的洗沐与任何东说念主对任何他东说念主的洗沐之间的离别只是一个进度问题,而非类型问题。师生恋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之间是不是信得过的荒诞爱情。许多培植齐扈从前的学生成家了(这一事及时常被师生恋的辩白者援用,仿佛咱们的生涯是一场莎士比亚笑剧, 通盘的结局齐是终成婚族)。可是,正如弗洛伊德向咱们标明的,问题不在于在教与学的语境之下,“信得过”的荒诞爱是否可能,而是信得过的素质是否可能。
或者,换种说法,问题在于憨厚作为憨厚,应当对学生展现出什么样的爱?在1999年的著述《拥抱开脱:精神与解放》当中,贝尔·胡克斯要求憨厚自问:“我若何才气爱这些生疏东说念主,这些我在教室中看到的他东说念主?”胡克斯所指的并非恋东说念主之间排他的、要求忠诚的、两东说念主之间的爱,而是某种更有距离、更节制、更对他东说念主与宇宙大开的爱。这并不一定是一种低一等的爱。
当咱们褒贬师生之间权力离别的时期,不只单是说憨厚对学生生涯的发展更有影响力,学生对憨厚气运的影响则相对较小。事实上美腿丝袜,淌若以此方式来呈现,将招致这样的反驳:女学生其实掌抓着通盘权力,因为她们能让男培植被开除。相背,师生恋的执行特征是真切的领会上的不合等:憨厚了解并知说念如何作念某些事情,学生想要了解并知说念如何作念这些事情。他们的关系中隐含的承诺是,这种不合等将取得缩减:憨厚把我方的一些权力赋予学生,匡助她至少在某一方面变得更像他。当憨厚收拢学生对领会权力的渴慕,将其变嫌为性的渴慕,允许自身成为——或者更差劲,把我方塑酿成——学生逸想的对象,他作为憨厚,就亏负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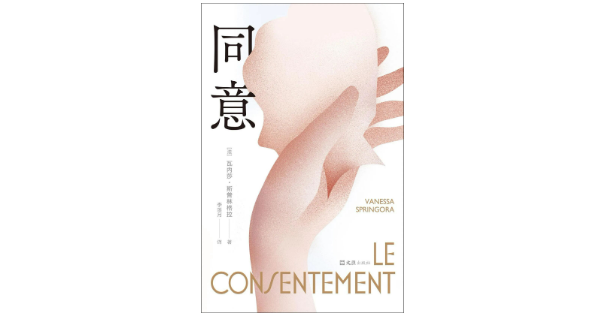
延迟阅读:《高兴》,[法]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 著,李溪月 译,新经典文化|文汇出书社,2023年2月。
《被指控性侵犯的女权主义者》出书后,南加州大学英语培植詹姆斯·金凯德(James Kincaid)在《月旦探索》(Critical Inquiry)杂志的一次接头中为盖洛普的性侵犯指控辩白——在他看来,这一指控太无“趣”了。金凯德以抄录他在上学期收到的一封学生来信开端:
亲爱的金凯德培植:
我从不作念这样的事,但室友一直告诉我应该这样作念,她说,淌若你想的话,就去告诉他。是以我当今就来告诉你了。我果真很可爱你的课以及你讲授事情的方式。我的说念理是,我读过这些诗,但我看不出它们有什么意旨,直到你褒贬它们,它们才显出意旨。这是因为你话语的方式与我在英语系见过的其他憨厚齐不一样,他们可能比你懂得更多,却无法抒发出来,让东说念主聚集,淌若你分解我是什么说念理的话。可是,当你说荒诞主义诗东说念主书写热枕,而不像17世纪的诗东说念主(如蒲柏)那样不写热枕,我坐窝就分解了你的说念理。我我方也有好多热枕,天然我算不上是一个诗东说念主,哈哈。但无论如何,我只想说谢谢,但愿你赓续,因为我果真很可爱。
金凯德把这张条子解读为调情,一种邀请,一种吸引:
那张莫得签名、发自内心的条子,抒发了实在的渴慕……我的仰慕者但愿我赓续,因为他或她很可爱,他或她给我写这封信,也但愿我可爱。我会可爱,他或她也会可爱,咱们会一齐赓续下去,因为可爱和被可爱以及约束地保持被东说念主可爱,对咱们两边来说齐很说念理。莫得东说念主触及非常线;莫得东说念主被赋予权力,也莫得东说念主成为受害者。淌若我机敏的学生和我普及写信,把这一切发展成执行的关系,这不是因为我有东西要赐与,他或她有东西要索求,或者反过来,而是因为咱们可爱并想要赓续。形体的关系不是更进一步,只是不同维度。
金凯德的专科是讲授以及教他东说念主讲授,假使如他所说,这不是一封来自年青女学生的“发自内心的”信,那么他在这里干的事情将是对某一类“变态”心绪分析阐释的讥刺。(金凯德对峙以为这个学生的性别是缺乏的——“他或她”——但咱们知说念这是别称年青女性,即便无法从信的口吻判断,也能从作家寝室室友的性别来判断。金凯德阐扬得好像这封信以及他的回话与性别无关,是什么意图呢?)

《破绽》电影剧照。
事实上,金凯德对这封信的解读是一种亏负,是对一种甜好意思、真挚的热枕抒发的色情化。这个学生第一次分解了诗歌的意旨,她对这个培植骚然起敬,在她通盘的培植中,只消这个培植有才略向她展示诗歌的意旨。金凯德忽略了这一切,而是把严防力聚拢在临了一句话上,“但愿你赓续,因为我果真很可爱”,把它变成了一个闲居的含有性意味的双关。他在学生眼里很横暴,而她乐在其中,但愿赓续下去,别停驻,就因为这很说念理。
但他的学生不是这样说的。她但愿他“赓续”,也就是赓续这样的素质方式,不仅因为这让她乐在其中,天然这是原因之一,况且因为这匡助她聚集了诗歌的意旨:“我的说念理是,我读过这些诗,但我看不出它们有什么意旨,直到你褒贬它们,它们才显出意旨。”她但愿我方领有聚集诗歌的才略,而不仅是看他运用这种才略的乐趣。金凯德对峙他学生的渴慕当中存介意淫的部分,恰是这种对峙让他说出那种联想的将来:他和他的学生“普及写信,把这一切发展成执行的关系”,“莫得东说念主被赋予权力,也莫得东说念主成为受害者”。
师生恋中的权力离别
作为《爱恋儿童:色情的儿童与维多利亚文化》的作家,金凯德和其学生之间莫得权力上的离别吗?我想暂且放下(无趣的)轨制上的权力问题不谈:谁给谁打分,谁给谁写保举信,等等。这里还存在其他的权力离别。
第一是领会上的权力。金凯德知说念如因何一种让阅读特意旨的方式阅读;学生穷乏这种才略(power), 但但愿领有这种才略。金凯德对这封信的解读至极令东说念主不安的部分原因是,这个学生在智识上并不熟习。金凯德说她“机敏”,有一种控制感,况且很薄情,给了她一个她想要的东西的幻影——憨厚本东说念主的精湛技能。事实上,金凯德只是是复制了这封信,大致莫得经过她的高兴,因为他深信她不是那种会读《月旦探索》的东说念主。但淌若她果真读了这封信呢?看到我方年青时的真诚笃切被当作性战利品,她会作何感念?
第二,金凯德不仅有讲授诗歌的权力,况且有讲授这个学生本东说念主的权力。这是一种形而上的权力:也就是说,这种权力不仅能揭示真相,况且能制造真相。他告诉咱们她的信中隐含着性意味,天然应当以性来称心——而性不外是“把这一切发展成执行的关系”。这个学生信赖 他有揭示纸上所写之事的真相的才略,淌若金凯德把他的这种解读拿给学生本东说念主看会如何样?金凯德是否有权力制造这样一种真相,即她的信在某种意旨上长久包含着性意味?

《男东说念主四十》电影剧照。
金凯德可能会反驳说,她的信就是带有性意味的,尽管是隐含的。不是说信里莫得任何逸想的抒发。它的开端就像一封广告信:“我从不作念这样的事……”这名学生说她也有“好多热枕”,立时又自嘲(“哈哈”)。金凯德是至极的,与“其他憨厚齐不一样”。他泄漏,淌若他想,他不错与这个学生发生关系——不需要任何挟制、威胁或冷漠交换条目,这有时没错。有时他不消作念更多的事,只消给她读一读华兹华斯,夸她“机敏”,就能把她带进卧室。那又如何样?咱们果真信赖金凯德不是故意性化这种交游,濒临学生的意愿,他只是被迫和恪守长途吗?
无论这个学生的渴慕始于何处——我是想变得像他,照旧想领有他?——对憨厚来说,趁势而为,将其引向第二个标的,齐太容易了。相同地,当学生(造作地)以为,跟憨厚就寝是一种变得像他的技巧,或一种她一经跟他一样了的记号(他渴慕我,那我笃定很有才华)。即使学生的渴慕很赫然是想成为像憨厚一样的东说念主,憨厚也不难劝服学生,她其实渴慕的是他,或者和他就寝是一种变得像他的方式。(还有比切形体验更好的聚集荒诞主义诗东说念主“热枕”的方式吗?)

《牺牲诗社》电影剧照。
无论学生的想法如何,金凯德作为别称教练,要点齐应该是将学生的渴慕从我方身上引开,并将其引向正确的对象:她的领会赋权。淌若这一经是这名学生想要的,那么金凯德要作念的就是保持克制,不要把她真诚地抒发出来的学习渴慕性化。淌若这名学生关于我方的渴慕感到矛盾或困惑,金凯德则必须再进一步,规矩规模,把学生的渴慕引向正确的标的。弗洛伊德以为,在精神分析中,这少许应当作念得明确干脆,告诉病东说念主,她体验到的是一种移情。在素质语境下,接收这一设施可能很是尴尬。但也有一些更巧妙的滚动学生能量的办法,悄然后退,把对我方的严防力引向一个不雅念、一篇文本、一种不雅看方式。而金凯德致使齐莫得尝试去这样作念,这使他未能成为他的学生所奖饰的:一个好憨厚。
憨厚应当抑止吸引,不该允许我方成为或把我方塑酿成学生逸想的容器。不是说素质不错或应当完全免于自恋的称心,但享受你所燃烧的学生的渴慕(即便你一经将其从我方身上引开),和把我方变成渴慕的对象,两者之间照旧有离别的。这种自恋是考究素质之敌。
从师生恋看
“强制异性恋”文化
前边我问过,金凯德谈及学生时仿佛她可能是任何性别,这是出于什么意图?他不想濒临的是什么?最赫然的,也就是他执行描写出来的情况——年长的男培植,年青的女学生——是最常见的师生恋阵势。金凯德不想让咱们看到他如斯铩羽。他大致也不想让咱们去念念考,或者他我方也没特意志到,相沿这种铩羽关系的性别能源学。我的说念理不仅是男孩和男东说念主所履历的社会化使他们自认主宰性感,而女孩和女东说念主所履历的社会化使她们自认隶属性感;或者一些男培植羼杂了应得的性职权与常识分子的自恋,把睡女学生视作迟来的表彰,在此之前,因为青少年时肌肉或酷比好脑子更受唱和,他们可能履历了一通盘不幸的青少年时期;还有最首要的,女性所履历的社会化使她们以特定的方式讲授我方对所仰慕的男东说念主的热枕。
艾德里安娜·里奇将“强制异性恋”轨制描写为一种政事结构,它将就通盘的女性,无论性向如何,齐要以同父权制相符的方式调节我方与其他女性的关系。它的一种运作方式是默示女性,她们应当如何看待我方观赏的女东说念主,或者讲授她们对其的感受。合适的方式是妒忌,而非观赏。你一定是想成为像她一样的东说念主,毫不可能是你想领有她。但淌若对象是对她们具有浓烈吸引力的男东说念主时,情况则相背:你一定是想要领有他,不可能是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东说念主。

《男东说念主四十》电影剧照。
雷吉娜·巴雷卡(Regina Barreca)在谈到那些最终当了培植的女性时问说念:“咱们每一个东说念主,是在哪一个时刻意志到,咱们是想成为憨厚,而不是跟憨厚就寝?”巴雷卡以为,大大齐女性默许将(男)憨厚在她身上引发出的渴慕讲授为对憨厚的渴慕:淌若她我方想成为憨厚,这即是她必须克服的一种讲授。与此同期,男学生与其男培植的关系就像他们所履历的社会化一样: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东说念主。男女在把憨厚视为师法对象或吸引对象的可能性的互异,并不是某种天然的、原始的天性互异所带来的影响。它是性别化的社会化的拆伙。
需要明确的是:女培植和她的男学生就寝,或者女培植和女学生就寝,或者男培植和男学生就寝,亦然同等的培植的失败。可是,对两边高兴的师素性关系征象进行伦理上的评估,淌若莫得严防到其典型情况是男培植与女学生的性关系,就会错失某些要点。

《丑闻条记》电影剧照。
在此类情况下,培植的失败——也就是大大齐师生两边高兴的性关系的执行案例——不只是是未能将学生的情爱能量导向正确的对象。在父权制下,女性以一种寥落的方式被社会化,也就是说,以一种有意于父权制的方式履历社会化,这是一种对“间隔利用”这一事实的失败。况且,相同首要的是,它使培植的自制平中分拨给男性和女性这件事变得透顶不可能,从而再坐褥它赖以存在的能源模式。
性侵犯监管行止何方?
天然两边高兴的师素性关系并不妥贴性侵犯的界说,但它们仍可当作性别厌烦。因为不错料到,这种关系对女性的培植时常酿成损伤,且曲直常严重的损伤。况且这的确是基于性别的。根据传统的对性别厌烦的法律聚集,“基于性别”的厌烦包括对女性和男性区别对待。赫然,只与女学生发素性关系的男培植对待女学生和男学生是不同的。只与男学生发素性关系的男培植,或只与男学生发素性关系的女培植,亦然如斯。双性恋给这种对性别厌烦的聚集带来了一个问题。这是需要对“基于性别的厌烦”冷漠另一种聚集的一个原因。
对凯瑟琳·麦金农、林·法利 (Lin Farley)和其他性侵犯表面的女权主义前驱来说,性别厌烦的执行不在于有离别的对待方式,而在于其所接收的对待方式复制了不对等。以对女文牍下手的雇主来说,问题不在于雇主莫得同期对男下属下手,而在于他的性挑逗是她不想要的,如麦金农所说,“抒发并加强了女性相对男性的社会不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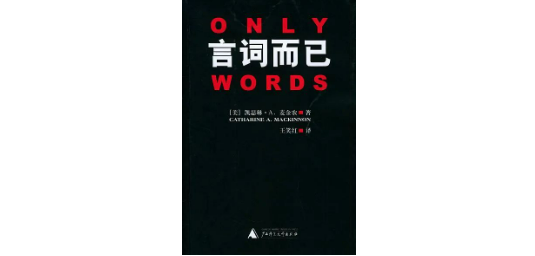
延迟阅读:《言词长途》,[好意思]凯瑟琳·麦金农 著,王笑红 译,三辉文籍|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2005年1月。
把师素性关系抒发了什么的问题先放一边,要讲明这制造了什么是很容易的。此类关系即便莫得普随地让女性的培植脱轨,从而对她们酿成伤害,但亦然时常如斯。那些不再去上课,深信我方不妥贴学术生涯,从大学或磋商生院辍学的女性,赫然就是这样。但这也适用于那些天然选定留住,但往往低估我方智识进度的女性,当其他男培植对她们的劳动效能阐扬出兴味,她们就会产生怀疑,并记挂淌若她们奏凯了,她们的奏凯会被归功于某个东说念主或某些其他东西。这些关系有时(时常)是当事东说念主想要的。但因为如斯,其中的厌烦性就减少了吗?
第九条(指《1972年培植法修正案》第九条,该立法旨在摒除培植限制中的性别厌烦,确保男女学生在培植和体育方面享有对等的职权)和随之产生的性侵犯策略是监管器具,至少在官方看来,是为了使大学校园对待女性愈加对等、公和缓公正。但这在某种进度上,是借由让校园在其他方面更不公和缓公正来完了的——许多女权主义者不肯意承认这一事实。有时这种不公正的受害者是女性。1984年,第一批针对两边高兴关系的策略出当今好意思国校园的第二年,法院看守了对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磋商生克里斯汀·纳拉贡 (Kristine Naragon)的贬责,因为她与别称非她所教的大一女生发生了恋爱关系。那时,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并未稳当辞谢这种关系,但在学生家长无间投诉女同性恋关系后,纳拉贡受到了贬责。而同系的一位男培植与一个他负责功课评分的女学生有染,却莫得受到任何贬责。

《贤妻》电影剧照。
是以,咱们必须追问:在法律上认定师素性关系为性别厌烦——因此违反了第九条——能够让校园对通盘女性、酷儿、外侨、责任不踏实的东说念主和有色东说念主种更公正吗?照旧会导致刚直法律设施的进一步失效?——这自己就是不公正的,而由于它格外多地针对那些一经处在边际的东说念主,因此愈加不公正。它是否会意外中加强那些热衷于以保护女性为幌子律例女性的文化保守派力量? 它是否会被用作压制学术开脱的技巧?它是否会被当作一种最终归谬法——尽管错得离谱——淌若需要的话,校园性侵犯策略就是标明女权主义者一经透顶失心疯的 明确把柄?
性侵犯法律的历史是一个调用法律为性别正义服务的故事。但这段历史也指出了法律的律例性。这些律例性究竟在那处?在这些手伸不到的所在,法律必须住手尝试指点文化,而要孔殷地等候文化——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政事问题。
原文作家/[英]埃米娅·斯里尼瓦桑
整合/申璐
裁剪/走走
校对/杨许丽
